你只知道有盲人按摩,却不知道还有7000万残疾人没有工作


中国有将近一亿残疾人,为什么在大街上却很难看到?
几年前,这个话题曾在互联网上激起过不小的波澜。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今年的主题为——更好地重建:朝着一个包容残疾人、无障碍和可持续发展的后新冠肺炎疫情世界。
面对残疾人,我们常常会自诩“正常人”,就像面对所有跟主流面目不同的群体时一样。
然而,人并不是总能站在大多数人那一边的。
在一些人眼里,残疾人甚至连“同情”都不配得到,留给他们的,是“指责”乃至“诅咒”。
“你一个盲人,出门干什么?”
这一切,还要从一位盲人网友的遭遇说起。
这位网名叫“盲探-小龙蛋”的网友,真名叫郑锐,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了自己坐电梯时遇到的不便,意外地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从视频来看,这部电梯既没有语音播报也没有盲文标识,导致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去到了哪一层。

事实上,出行时处处不便,已经是国内残障人士的日常了。
所以他也只是苦笑着说一句“哎呀,太难了”,并表示“希望以后公共场所的电梯能够更加人性化一些”。

然而,就是这样一条日常生活的记录,让他被评论区的网友们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通。
有人语重心长地讲述“社会是为大众服务的,大众都是正常人,(公共设施)有就用,没有,也不是该为你准备的”的宇宙真理,试图让残障人士摆正自己的位置。

也有人像是刚在KTV嚎完一首《凡人歌》,那股看破人生的劲儿还没过去,张嘴就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少数人改变。


还有人发出了终极一问:你一个盲人,你出门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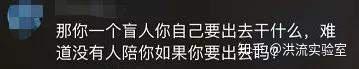
评论区的众生相,在集体无意识的催眠下显得无比正当。直到这条视频连同底下的评论被转发到微博上,习惯了政治正确叙事的人们才发现——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是会带着恶意与偏见去看待残障人士的。
7000多万残疾人没有工作
郑锐是一名信息无障碍工程师和培训师,每天转三趟地铁上班,到了办公室,精准地触摸并打开会议室电灯的开关,吃完午饭,有时去同事座位上唠唠嗑。他常说,自己和明眼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将目光放到全国,他确实是相对幸运的那一个。根据统计,我国目前八千多万残疾人中,只有不到一千万人拥有稳定的工作。
无论是云客服,还是外卖骑手,抑或是街角盲人按摩店的按摩师傅,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残疾人,都已经是这一群体中状况最好的那一小部分。
冰山之下,还有多少残疾人在镜头没能照见的地方踽踽独行?
2020年的开年纪录片《人生第一次》记录了不同人群在人生重要节点的“第一次”:出生、上学、结婚、买房……

然而,真正让它出圈的,却是第五集《上班》。
它本可以将镜头对准大学生,毕竟,完成学业,走入社会,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这次,它选择记录残疾人们的生活,一种让我们感到陌生却又与我们近在咫尺的生活。

坐落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的残友培训就业孵化基地,是王绍军上班的地方。
每天早上,闹铃声响起,陪护小哥熟练地赶来帮王绍军换好衣服,再抱他离开床,坐上轮椅,去上班。

常人眼中很近的一段路程,对于在这里上班的人来说,都要颇费一番周折。
这个由王绍军一手创办的培训基地,先后为四千余名残疾人提供免费培训,直到他们技能测试合格,成为一名云客服。
镜头记录下,这群云客服与顾客的对话常常很无聊,有时候他们甚至还要被辱骂,可就这样,他们竟然还有一些享受。
因为在这个时候,世界是真的把他们当作了正常人,有情绪就在他们身上发。

这比那种异样眼光下的廉价同情要高贵得多,这是真正的平等。
没有把他当成残疾人,也就没有怜悯,没有特殊对待,更没有歧视。
腾讯公益助残疾人就业
在全球各地,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存在某种形式的身体或精神障碍。他们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少数派。
可数量如此庞大的残疾人,仿佛都在公共生活之外,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2008年,我国政府签署并批准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项公约的目标,就是把人们对残疾人的看法从“社会扶助的对象”,转变为“享受各项权利的主体”。

《触不可及》剧照
但十几年过去,残疾人实际上还是免不了被安排的命运。
在特殊教育体系中,聋哑学生往往被送入专门的中等或高等职业院校。这些地方提供音乐、绘画或按摩课程,也就是外界认为适合残疾人的工作。
自2008年有统计以来,中国残联每年发布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盲人按摩事业稳步发展”都是“就业”板块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视力残疾在所有残疾人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5%。
不得不说,这是对残疾人擅长领域的刻板印象。
一提到“盲人”就想到“按摩”,但盲人真的比普通人更适合做按摩吗?盲人是不是只能做按摩?如果不想学按摩,那他们还可以选择做什么?

事实上,他们的选择非常有限。
一方面,如果他们希望尝试主流的教育与就业道路,就会面临巨大的障碍。
一般来说,将残疾人拦在就业市场之外的,是来自心理、物理、结构三方面的阻碍。被歧视、被排斥,是残疾人在工作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另一方面,残疾人的数量还在持续增长,传统的集中就业、按比例就业政策,越来越无法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的就业需求。
为帮助残疾人更好地就业,安溪县残联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发起《扶持残疾人就业计划》,筹款目标为638435元,已收到1567份善款,累计金额超过18万元。

对残疾人而言,要想生存下去,他们需要付出数百倍于常人的汗水和努力。他们非常明白自己的劣势。因此,他们珍惜每一个学习专业知识、工作技能的机会。
安溪县残联志愿者们对每位残障人士进行至少每周一次的一对一心理疏导,教他们手工制作、打包装,以及运作电商平台。
黄某因意外脊椎损伤、高位截瘫,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黄某在安溪县残联的帮助下,成功运营自己的网店,不但解决了就业问题,同时还帮助到身边的残疾人。
除了帮助残疾人掌握工作技能,腾讯公益还帮助丢了饭碗的残疾人重新就业。
今年年初,受疫情冲击,盲人按摩业受影响很大,很多盲人按摩师基本都“失业”了。

普通人是失业,对于盲人则是等着饿死。
一个叫蔡勇斌的盲人工程师,想为这20万盲人按摩师做点事。
蔡勇斌初步的打算是做一个盲人知识学习平台。疫情期间,有知识的视障人士可以在上面讲课赚钱,赋闲的盲人可以免费学习保健按摩、编程等知识。等疫情过后,这个模式也可以继续运营下去。
然而问题来了,开发的成本和讲师的课酬,从哪里来?
蔡勇斌给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发了一条微信,汤道生将这段聊天转给腾讯基金会的负责人。在腾讯投入的15亿“战疫基金”里,包含了对战疫程序开发者的支持,也包括了孤寡老人、社会孤儿、重病重残等受疫情影响的特殊困难人员的帮扶。
蔡勇斌刚好都属于这两类人群——在残障人群里,具备程序开发能力,并且其开发的程序,又可以帮扶到盲人这个残障人群。

经过评估,腾讯基金会决定出资捐助蔡勇斌的线上有声培训APP项目。这笔钱可以帮他完成产品研发、上线、上云服务器,以及支付给讲师的第一批课酬。
中国有1731万视障者,如果蔡勇斌的App能打造成功,就可以让视障者有机会在互联网时代无障碍通行,“看见”全世界了。
在上海,也有一家叫“熊爪”的咖啡馆,店员通过“熊爪”将咖啡从“洞口”递出,顾客还可以与“熊爪”互动。这家店里,咖啡师是聋哑人,用熊爪递咖啡的店员是面部烧伤者。

咖啡店创始人说,希望通过开办这样的店,给残障人士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关爱和尊重残疾人
对于年轻的残疾人而言,解决生计或许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但对于老年残疾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关爱和陪伴。
80岁的刘婆婆是成都一个乡村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身患残疾多年,每月依靠580元的五保金来勉强维持生活和医药开支,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在这家敬老院,像刘婆婆一样的孤寡老人有35位。

春节期间,合家祈福游玩、团聚喜乐、处处洋溢着喜气。但是对于贫苦的残障人群来说,春节和平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他们内心依然渴望陪伴、问候和关心。
临近年底,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发起了《2021陪残疾人过年》活动。该项目覆盖四川500户残疾人家庭,计划送上春联、米、油、牛奶等年货,以及每户300元的现金。
志愿者们还会开展线下活动,为残障人士举办暖心活动,陪伴残障家庭,让他们也能感受到过年的气氛。该项目计划筹款340800元,目前已收到430份善款。
在腾讯公益平台上,与残障人士相关的公益项目还有很多,譬如《残疾人文艺基地》、《扶助贫困残疾人》、《残疾人温暖工程》等。腾讯公益给这些项目提供了宣传和筹款的渠道,为守护残疾人事业作贡献。

生而健全,是我们侥幸。但当我们老去,与我们朝夕相伴的,比起子女,更有可能是各种程度上的残疾。
关爱和尊重残疾人,正视他们的需求,没那么难。帮助别人,也可能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就如同腾讯公益平台一直所倡导的,世界更美好,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而是每个人做了一点点。
